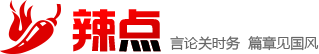
- 0731-82965630
- 群:118373795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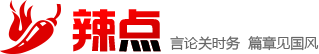

5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,6月1日起,被称为“史上最严控烟条例”的《北京市控烟条例》将正式实施。该条例可以理解为“凡是有屋顶的地方都不能抽烟”,违者将处罚款。但我国自2003年签署《烟草控制框架公约》以来,2004至2014年,全国卷烟生产不降反增,十一年生产卷烟近25万亿支,十一年间增加了7353.92亿支,增长率39%。
对无法“脱瘾”的控烟且慢称“最严”
笔者觉得这种控烟措施谈不上最严,是因为最严的措施是不留余地的。而在烟草销售店随处可见,而且大多装潢的很有档次,货源充足,大量供应的市面上,哪里能看出一点控烟的社会氛围?而被誉为凸显政府控烟决心的“税价联动”,这点不痛不痒的提价,能让“烟民”望而却步的话,卷烟也就称不上“香烟”了,戒烟也就如少出一块肉那样无所谓了。虽然不知“烟瘾”在生理上的具体作用,但依赖性的毋容置疑的。
当一项有关全民健康的控烟措施,在保证烟草业既得利益的前提下,光指望“烟民”脱瘾,烟草业丝毫不受“戒烟之苦”,那么,只要烟草业还能保持原有的丰厚利润,控烟几乎是一句空话。无需去百度“烟瘾”是什么意思,只要看烟草业对此的无法割舍,就不难理解什么叫“依赖性”。按理来说,既然控烟作为政府号召,谁应该先做出表率?谁应该先表现出“忍痛割爱”的决心?而且,烟草业一旦忍痛割爱,烟民就如“无米之炊”了。 [详细]
最严控烟手段,别只“招呼”烟民
仔细想想,罚款、增税等“最严”控烟手段,全都一股脑地“招呼”到烟民头上。烟草部门有两副面孔:对民众解释说,我收烟民的税,我罚烟民的款;对烟民暗示说,民众禁烟呼声太高,你多掏钱点配合一下,鼓励甚至诱惑他们买烟。如此左右逢源,既堵了民众要求控烟的舆论,又挣了烟民手里的钱。“最严”控烟一旦遭遇政企不分,反而成了烟草业装点门面的旗号,成为摸着石头不过河的借口。
简而言之,主导控烟者却是控烟的最大阻力,他们制造了一个畸形的垄断市场,为保证利润和税收,限制烟民的同时又保护他们,像极了老顽童周伯通的左右互搏术。毫无疑问,这也是种种“最严”控烟手段都针对烟民而非烟草企业和主管部门的根本原因,因为他们一边制定规则一边控制市场,根本不把民众为烟草付出的健康等社会代价当回事儿,更何谈补偿。 [详细]
就算号称“史上最严禁烟令”的行政之手与经济策略联姻,我想这还不够。至少还有一点要认清并唤醒,即受害者抵制吸烟的“主体意识”。禁烟控烟最主要的意义是确保非吸烟者的权益,那么,对这些没有涉及社会公共安全的权益维护,就需要形成一种受吸烟影响者或“吸二手烟者”为主体的维权意识,而非绝对地依赖政府行政力量,或一味被动等待来自政府部门的权利救济。事实上很遗憾的是,当前对受吸烟危害群体的权利救济几乎也是一片真空。
换言之,政府部门不仅仅要制定控烟条例,更要从从制度与法律上,充分给予民众自主自觉抵制时免受伤害。可以肯定地说,以前各地一个个“最严禁烟令”无效,除了因为这些禁烟令独孤一身,没有形成行政、经济、法律等各手段相结合的系统性支撑外,最重要的原因还有,公开抵制吸烟的行为成本太高,最严禁令的“严”与广大受吸烟影响者自主的权利无关。[详细]
烟草不减产,控烟是笑谈
既肯定控烟要从源头上控制,认为罚款解决不了根本问题,又对减少卷烟的生产态度纠结暧昧,这也许是地方政府的真实写照。利益的纠缠成为中国控烟的最大问题。很难想象,中国的控烟履约机构是烟草专卖局,壮士断臂的勇气不是谁都有的,所以你看,中国到现在还没有在烟草制品的包装盒上印制醒目、清晰、画面较大的黑肺、烂牙、病容等警示图案,尽管民间的呼吁已经好多年!
管办不分、政企不分的体制,导致控烟无法摆脱烟草企业利益的影响。控烟要先形成积极地控烟氛围当然没有错,但有一点应该明确的是,烟瘾不同于毒瘾,戒烟不需要太多的勇气和毅力,更多的是一种习惯,减少烟草的销售不会引发社会问题。所以,控烟首先要做的是打破烟草的利益绑架,只有先打破了这种固化的利益,从源头上减少烟草的生产,严防烟草进口,再辅之以控烟宣传,加大处罚,如此,才有可能逐步控制烟民数量,助国民养成健康的习惯。[详细]
尽管一个接一个控烟令出台,但控烟效果一直平平。回望过往,政府部门似乎为控烟“操碎了心”,但仔细一想基本都是招呼在了烟民头上,却鲜见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革自己的命。不说减少甚至停止烟草生产,就连在烟盒之上印上醒目的警示标识,各方呼吁许久也未见回应。总之,目前的控烟行动,并未让人看见诚意与决心,看来“控烟难,难于上青天”的喟叹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了。